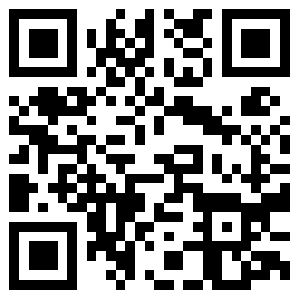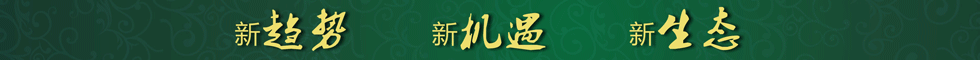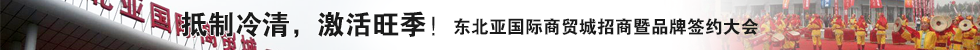原標題:市場決定論下 陶瓷或是佛山要邁的頭道坎
最近發生在佛山陶瓷行業的兩件事,分別從政府和市場兩方面回答了傳統產業陶瓷的去留問題。陶瓷或將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市場決定論下佛山要經歷的第一重檢驗。
第一件事是,在政府強有力的干預下,石灣金意陶終于停產待遷。金意陶經過近10年的發展,已成長為知名品牌。自2008年至今投入600多萬元實施整治,先后采取了清潔能源改造、完善尾氣治理設施、在線監控及削減產能等舉措,污染物排放達標,卻依舊難容于佛山中心城區禪城,最終不得不遷走。在搬遷調研會上,金意陶老板關心的不是搬遷問題,而是政府到底還要不要陶瓷企業。
第二件事是,佛山最著名的陶瓷龍頭企業東鵬終于上市,卻上演了一幕“陶走”清遠的戲碼。而就在東鵬傳出上市消息的前一周,東鵬陶瓷黨委書記王思平曾當面向佛山市委書記李貽偉提要求:“東鵬目前在禪城的兩個車間都在不斷縮小,有兩個項目已立項但缺地。目前有外市在尋求幫助落地這兩個項目,但東鵬還是希望扎根于佛山本地發展。”截至目前,東鵬的用地要求尚未被滿足。
這兩件事反映出三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城市化與佛山陶瓷究竟能否共存?大企業的予取予求政府如何應對?制造環節外遷后是否真能保住總部?
第一個問題其實就是陶瓷當下還適不適合佛山。此前禪城區曾在10月公布的《佛山市禪城區陶瓷產業發展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給予肯定答復。該征求意見提出:將南莊定位為建筑衛生陶瓷產業功能區,石灣為陶瓷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禪城擬專門設立由區和鎮街主要領導掛帥的陶瓷產業提升辦公室,努力將全球最大的陶瓷制造業基地建設成為全球最大的陶瓷現代服務業聚集基地,打造“世界陶瓷之都”。這份《意見》中政府之手的痕跡隨處可見,在市場決定論的視角下重新審視,《意見》中的目標恐怕很難實現。從金意陶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現有的生產工藝水平下,即便企業盡很大的努力減低污染,控污效果依然無法滿足城市生活環境的需求。即使企業勉強留下,也會被天然氣等高額的控污成本擠壓窒息。自佛山得名以來的上下千年,陶瓷一直是無可爭議的名片,但是伴隨佛山的名字從季華鄉變成大都市,市場之手越來越急迫地想修改陶瓷這張名片。如何看待城市化與陶瓷之間的矛盾,是否有必要伸手化解,是佛山和禪城兩級政府要面對的考驗。
第二個問題,可以用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的關系作比。東鵬無疑是佛山陶瓷業的巨頭,而事實上,在歷經2008年“創模”之后,留在佛山的陶企基本都是行業的佼佼者。這些陶瓷企業上規模、納稅多、品牌知名度高、市場競爭力強,省內周邊乃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在緊盯著佛山的產業升級政策和企業動向,欲找機會將這些陶瓷企業招商引資過去。東鵬所在的禪城,土地開發強度早已超標,已經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此時大型陶企提出用地需求,政府必然陷入兩難境地:給地難,不給地企業會“陶走”。其實,地方政府應以更超脫的心態對待大型陶企的去留,在合理的范圍內盡可能服務企業。如果仍不令企業滿意,那就隨它去吧。與此同時,企業家也應具備一定的家國情懷,不僅思考自身發展,也肩負與城市共榮的使命。否則即便向條件更豐厚的地方遷移,待該地方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也遲早會因同樣的問題再次搬遷。前不久成立的季華商務同盟會就是一個正面的例子。該同盟會反復強調的,不是通過同盟實現成員企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如何將季華路打造成國內知名CBD。市場決定論不是任由市場之手導致自發性弊端,而是政企間通過更良性的互動實現共贏。
第三個問題是,陶瓷制造環節與總部分離后,空心化問題是否真的可以通過政府之手避免。就此,總部經濟研究學者趙弘曾經用底特律集中汽車及零部件企業總部的例子為佛山打氣,可是底特律卻破產了。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集結的是電子信息總部,而非傳統制造。這幾年佛山陶瓷的展示環節也在向一級渠道前移,陶瓷總部剩下的還有研發、營銷、結算功能。由此可以看出,陶瓷總部對佛山的最大依賴就是城市環境。這個優勢短期內還無法被外遷地超越,再加上佛山陶瓷的城市名片,是目前佛山陶瓷可以抓住的兩個最大優勢。佛山要再做陶瓷文章,今后必得圍繞這兩點。